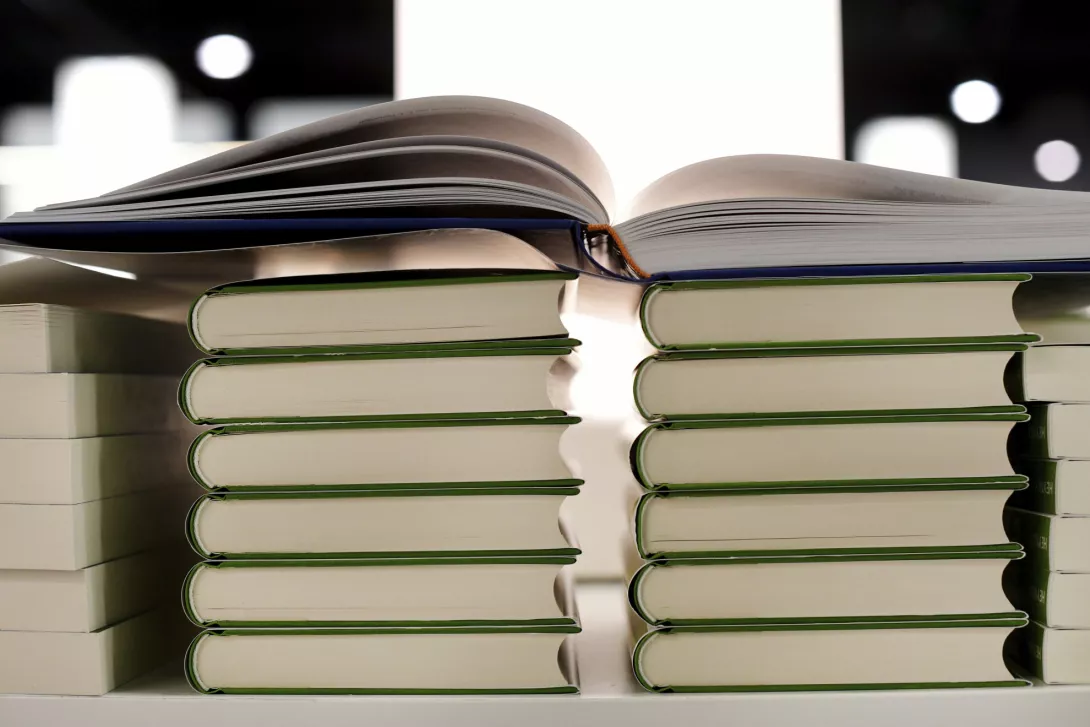
- 出版若要成為公共討論的一部分,須有其他媒介相呼應,讓新媒體成為合作夥伴。
- 政策的出發點,不是把出版業當成即將沉沒的船,而是協助打造新能力、新基礎建設。
- 台灣擁有華文世界最自由的出版環境,應該趁現在建立起有影響力的出版內容,與世界對話。
幾個月前我成立了新的出版社「有理文化」,得知的朋友和師長多半是在祝福中帶著憂慮,甚至是憂慮大過祝福。創業本身已經不容易,更何況挑選了一個前途堪慮的領域,此人若不是太傻就是太瘋。
這些憂慮其來有自,看看台灣出版業近年的景況,壞消息太多了,銷量下滑、書店關門、出版社收攤,各種指標似乎在在指向一個出版寒冬。我身邊仍有許多人喜愛買書、讀書,但世代習慣的差異、媒體生態的巨變,都是不可否認也難以逆轉的事實。人們難免想問:出版,真的還有未來嗎?
被問到這個問題時,我常會回答:只要人類文明還在,出版業就會在。這句話,一半是玩笑,一半也是認真的。
只是「出版」會改變。它從來不是一成不變。
對於與我同輩的編輯和從業人員而言,問題不是出版是否還有未來,而是如何能有未來。如果我們還要在這個行業待上二、三十年,甚至更長的時間,那我們勢必經歷這樣的思考實驗(或靈魂拷問):出版的未來到底會是什麼模樣?
我也常常在思考這個問題,想法很多,真要談起來,似乎一篇文章是不夠用的。但在此且讓我拋磚引玉,分享幾點初步的想法:
一、談出版的未來,必須分眾討論
首先要說明,出版並非單一市場,不同類型的書面對的情況與機會差異極大,未來也會長出不同樣貌。生活風格、商管、童書、人文社科,在讀者群、行銷方式、營收模式等方面都不同。就好像經營米其林餐廳、連鎖速食店與路邊小吃攤,各有各的定位,也各有各的挑戰,沒有誰好誰壞,也沒有哪個比較容易,總之不能輕易拿來相提並論或混為一談。
我在這裡談的,主要是以人文社科出版的角度來思考,因為這是我熟悉的領域,也是與本次主題「公共討論」比較相關的一環。
二、出版是仍能直接獲得讀者付費支持的內容產業
我過去經營網路媒體,出版業的朋友常羨慕我們流量大、聲量高,我常會解釋,流量雖高,但變現不易。大家習慣了在網路上看免費的東西(就如同您現在看的這一篇文章),要說服人掏錢是難之又難,所謂網路媒體的訂閱制,不過是最近幾年的事情,而且成功者屈指可數。網路媒體若是仰賴廣告,必然就變成要追隨流量,內容也就傾向追求即時回應、迎合大眾口味,甚至等而下之。
但出版不同,書籍出版是少數讀者已經建立付費習慣的內容產業,這很關鍵,因為這意味著出版社不必完全向廣告和流量邏輯低頭,能為深度或獨特,乃至於小眾的內容保留出經濟上可行的空間。
三、書籍的不可取代之處
同樣是從經營網路媒體獲得的心得:就在這幾年來,演算法的變化,使網路內容越來越碎片化。這樣的觀察,可能在五年前就已經出現,但讓人沒想到的是,碎片竟可以繼續破碎。
破碎而短暫。Youtube當紅之際,人們說影片要紅的秘訣是前七秒要夠精彩,而今短影音當道,恐怕連七秒都嫌長。這是而今社群媒體的特性,議題很難生存超過 48 小時,除非它被娛樂化、迷因化或簡化成口號。
但正因如此,書籍的系統性價值更顯得重要,能將散落的觀點加以編排,呈現碎片的全貌;它能提供脈絡,建構出能支撐思考與討論的框架。就我一個長期試圖在網路上提供(稍微具有)深度內容的作者而言,這一點,書籍仍然是無可取代的。一篇兩、三千字的文章,網路上稱之為必須慎入的長文,印在書上不過幾頁。
四、新媒體不是出版的競爭者,而是合作夥伴
當然,你可以說,上面兩點恐怕還是太理想了。如果一切都這麼美好,出版業又何來那麼多挑戰?
的確,新媒體的出現帶來許多挑戰。但新媒體不會取代舊媒體,只是會重塑整個媒介生態系。用白話文講,我們必須接受不會再有那麼多人讀書,也不會再有那麼多時間讀書了。
即便如此,出版與新媒體的關係不一定是相互對抗,而是思考書籍如何與其他媒介建立更多交集,互為引介。近年來在歐美興盛的 #BookTok 潮流,即是透過抖音上的短影音,帶動新一代年輕人的閱讀風潮。
我們的 BookToker 在哪裡?
五、數位帶來的不只是形式變化,還應該是策略變化
我的意思是,所謂的數位出版並不只是把紙本書變成電子書,還會重新定義發行、銷售以及與讀者的互動方式。
出版應該思考的不只是紙本書或電子書,而是如何與影像、聲音、互動平台形成互補互動的跨媒介內容。紙本書延伸成 podcast 系列、線上課程、互動網站——讓內容在不同媒介間流動,吸引不同入口的讀者。
但我想講的不只是電子書、有聲書、或是線上影音課程。這些都很重要,但那只是產品面的變化,除此之外,還有更多變化需要發生。比如,對於讀者輪廓的掌握。
六、出版的完成需要跨媒介支援
有個經典的哲學提問:假如一棵樹在森林裡倒下而沒有人在附近聽見,它算不算有發出聲音?
同樣地,假如一本書問世後沒有被閱讀和討論,它算有出版(published)嗎??
如果出版要成為公共討論的一部分,就必須有其他媒介與之呼應。書評專欄、深度訪談、線上讀書活動,甚至是跨平台的策展,延長書籍生命週期,讓它持續在公共議題中揮作用。今天的問題不是「書好不好」,而是「書沒有被好好談」。
書籍的生命不只在新書三個月宣傳期。我們需要更多專業書評平台、跨領域論壇、共讀社群,甚至與影像、劇場、展覽合作,線上加線下,讓閱讀成為一種持續的社會行動。
七、有些出版,無法靠市場
市場能夠支持暢銷書,但有些具備公共價值的出版計劃,不論是填補知識缺口、保存文化記憶、調查公共議題,都很可能無法單靠市場動能來推動。
但這並不是理由讓它們消失,而是需要尋找其他支持方式:公共資金、基金會贊助、與學術機構乃至於跨國合作,甚至將它們視為一種文化的基礎建設。不是所有問題都能靠市場來解決。近年來新聞媒體「報導者」的模式,應該也值得出版產業參考。
八、出版需要的不是救生圈
也得談談政府的角色。儘管出版業面臨諸多挑戰,我個人仍希望相關政策的出發點,不是把出版業當成一艘即將沉沒的船,而是思考如何打造能在新時代航行的戰艦,甚至是一支艦隊。這也許包括投資於數位基礎建設、培養跨媒體能力的編輯與創作者、推動國際交流、促進出版與教育、科技等不同領域的結合。
我們目前看到了許多分散的作為,但整體策略上仍有些模糊。
九、期待台灣原創思想的黃金年代
台灣擁有華文世界最自由的出版環境、多元的社會議題、豐富而獨特的歷史經驗。我們可以討論各種敏感議題,而不用擔心被審查或封殺,這理應是孕育新思想與原創論述的好環境。但我們的創作者與編輯,應該可以更有企圖心。就人文社科領域而言,我認為翻譯的作品仍然偏多(當然,翻譯書籍仍然重要),原創的作品太少,跟社會對話的作品太少,而有企圖引領時代思潮的作品就更少了。
自由很脆弱,如果不趁現在建立起有影響力的出版內容,未來沒有人能保證空間會不會有變化。所以,此時是最該努力的時刻。
十、我們的讀者不只在台灣
最後,台灣可以與世界對話。
有大量的華語讀者不在台灣,甚至不在中國,他們同樣需要、也願意閱讀高品質的華文內容。如同前面所說,數位出版帶來的不只是出版形式的變化,也是市場想像的重新繪製。當紙本跨境運輸的限制不再是問題,出版物的讀者群可以是整個全球華語社群,這意味著台灣原創內容的影響力與商業潛力都有全新可能。
甚至不只是華語讀者。AI 技術快速成長,讓不同語言間的轉換變得更加容易,門檻更低。比起以往,現在只要內容具備國際吸引力,更有機會觸及全球讀者。
喔,是的,AI,這篇文章講了這麼多,卻在最後才提到AI,恐怕出版的未來還有太多議題值得關注。但這篇文章已經超過了原定字數。
上述觀點必然不完整,有些也未必是新鮮的觀點。不過,關於出版未來要走向何方,這個問題本來就沒有單一的正確答案。唯一能確定的是,未來不是靠預測,而是靠創造。所以,讓我們繼續辯論、探索、嘗試,讓我們在失敗時學習,在成功時分享經驗,讓出版這件事本身也成為公共討論。